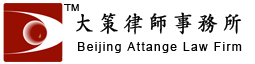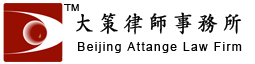故乡的印记
故乡其实应该是个农业社会的概念,我们说故乡时,大抵都是指“故土”或“乡土”,土地和天气决定了农业社会岁岁的收成,收成又决定了祖祖辈辈生存的丰度,而正是这丰度决定了我们对故乡的依恋。上学时读余光中或席慕容的《乡愁》、黄河浪的《故乡的榕树》,因为那时候还没离开故土,这些文字也无法挑逗我们对故乡的恋恋情感。而今,有空时重读这些文字,又觉得太过煽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外的游子大概都是因为故乡资源(不仅指自然资源,还包括社会资源)的贫瘠,才背井离乡去寻找认为更美的世俗生活。待那片土地离我们渐行渐远,喧嚣的尘世(城市)生活使我们不时感到疲乏时,故乡的那份单纯与熟悉便会在任意一个周末的残阳下映入我们迷惘的眼帘,其实谁都可以选择回归故里的生活,但您绝对会缺乏那份勇气,您肯定不会让当下生活的世界再次成为“故乡”。所以,过分的煽情只是自欺式的慰藉,故乡或许只能放在梦中。 大策随笔
我的故乡位于南方一个城乡结合地带的大农场,农场被一个用于灌溉的大型水库环绕着。农场里的一草一木、一沟一壑、一鸟一兽将童年的记忆装扮得绚烂缤纷。尽管农场住着几十户人家,但每次出门,碰到的鸟肯定比碰到的人还多。农场的山不高,林不深,野禽无法危机人的安全,哪个角落都可以成为我们一整天的乐园。南方的农村大多种两季水稻,暑假的时候,农民收割完早稻后,就得用水库的水来重新浇灌农田,以栽种晚稻的秧苗,水库的水位每天都会下降,没有及时感应水动的鱼儿便被留在浅滩的洼地里,记忆中很多个暑假的光阴都会随着这些鱼儿消逝得无影无踪。
有座较高的山峦将农场和周边的农村做了分界,有一处分界标志很是方便识记,就是立在一个基座上相互嵌得很牢固的三块条形石所组成的大门框,此门框为一古庙的残留建筑。世事变迁无常,古庙已经不知去向,碎瓦残垣也不曾遗留,只留下这条石门框历数寒暑更迭。记忆中最清晰的是石门框上的一副楹联:“万德一心法门原不二,峰回路转净土即此中”,离开故乡后游历过很多寺庙,每次看到寺庙中的各式对联,都会不由自主地拿来和这幅对联做对比。后来也曾刻意背读过不少措辞有味的对联,但至今记忆最深刻的还是这副对联。的确,曾经遮风避雨的庙宇已经不知去向,“不二法门”亦然还在;昔日念经诵禅的高僧或许升天成仙,“此中净土”至今未变。
水库的水位如今应该还是涨涨落落,哪些留在洼地的鱼儿们,还有人来打扰您们吗?!路过石门的行者匆匆来去,雕琢在石门上的对联,定有人停歇吟读吧?!
想起故乡,还是那轮明月,仍会朗朗照于心间。 大策随笔
作者:大策律师事务所 |